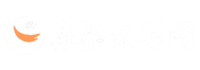- 莱州市光州东街678号 13583595082
- fdliang87@126.com
散文随笔
欢迎您阅读:难忘故乡盛夏夜
难忘故乡盛夏夜
儿时的记忆,越是久远便越发的清晰。胶东老家的盛夏夜,如一幅幅美丽的画卷,永远存于我的脑际。
如火的骄阳,喷射了一天的光和热,终于累了。它像一个大火球,慢腾腾地坠入了蔚蓝的大海。
在太阳坠落的地方,天水相连,一片片火焰似的彩霞呈扇面渐渐地淡开去。
在这个时候,家乡古老的村庄,高高低低的茅草房子,烟囱里灰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。天没有一丝风。那炊烟便徐徐地上升,然后慢慢地弥散开了,整个村庄也就笼罩在淡淡的灰白色的烟雾里。此刻一股燃烧过青草之类而发出的淡淡清香,也混合在这灰白色的烟雾中。
在这黄昏的暮色里,庄稼人三三两两的,或光着脊梁,或穿着汗衫,头戴斗笠,肩扛锄头,不紧不慢地走出了田间地头;几个男孩头戴苇篱,上面挂着几串蚂蚱,得意地骑在牛背上,从翠绿无边的田野上向村庄走来。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不大一会,袅袅的炊烟便慢慢散尽,随之夜幕也就徐徐地拉开。这个时候早有孩子们三个一伙,五个成群,叽叽喳喳地来到河边的树林里开始摸知了猴。知了们还在树上一个劲地高叫着: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孩子们瞪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,这儿瞅瞅,那儿摸摸,仔细地寻找着知了猴。树林好大一片,郁郁葱葱的。孩子们极有耐性地撒目着,寻找着,挨棵树干上摸索着。有捷足先登的知了猴们,已经爬到树干的分叉处,因为那时没有手电筒,孩子们很难发现它们……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么热衷于钻到树林里去摸知了猴,她们大都三五结伴,悄悄地来到离村子稍远一点的小河里,瞅瞅四下里没人,听听没有说话的声音,便偷偷地脱下衣衫,悄悄走进那清澈的河水里,然后轻轻地撩起清亮的河水,轻轻地洗洗那汗津津的身子。有时她们会你摸我一把,我抓你一下,互相泼水嬉戏。有时她们也会像男孩子那样用手捏着鼻子,学着扎猛子,有时她们还会喊个“一、二、三”,一齐把头扎进水里去,比比谁扎在水里的时间长。有时她们还会大着胆子摸索到河水较深处,学狗爬,打蓬蓬。水里的小鱼小虾们,便悄悄地凑近她们白嫩的身子,用嘴巴去亲吻她们那光洁的皮肤。女孩们却全然不觉,因为她们玩得兴致正高。可要是忽然听到有男孩的叽喳声,她们便会慌忙地跑上河沿,急三火四地穿上衣衫……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老街头,巷子口,南河沿,不知什么时候便亮起了一盏盏灯!这儿一盏,那儿一盏,黑暗的老村庄便睁开了眼睛。小小的煤油灯笼搁在方凳或杌子上,灯光并不太亮,但看着这一盏盏灯,让人从心里头感到敞亮,感到温馨,感到舒坦。哪里有亮光哪里就有人。每一盏灯的周围,都围坐着许多婆婆妈妈和大闺女小媳妇,她们都忙活着掐草编。在女人们的周边,便是些年纪不等的男人。他们有的坐着小板凳,有的坐着小马扎,还有的坐在草帘子上。他们悠闲地摇着蒲扇,嘴里叼着旱烟袋,忽明忽灭的,好像星星眨着眼睛。女人们有时窃窃低语,有时忽然朗声大笑起来。男人们便知道她们是在说些私密话。这时便有男人插上几句荤话,故意凑个热闹;有男人甚至打诨,说上一两个黄段子,便惹得男人和女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那些未出阁的闺女们,便羞涩地低下头去,故意憋住笑。但也有的忍俊不禁,嘻嘻地笑出声来;有的强忍着不笑,便憋得满脸通红,好一会才不好意思地抬起头。有中年男人便乘机打趣:哈哈,不用装正经,心里偷着想,更是不得了。哼,早晚有一天,黄花大闺女也会变成小媳妇啊!几句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村头那棵老槐树下,那盏灯的周边围拢了不少人。远远就能听见有人在拉胡琴,听见有女声在随着胡琴唱着“李二嫂眼含泪……”。那胡琴拉得还算靠谱,可那唱腔却有些跑调。那女的刚刚唱完,便有掌声立刻响起来,随之有人大声喊:“唱得好不好?”大家齐声说:“好!”“再来一段要不要?”大伙又不约而同地喊:“要!……”
顺着弯曲的小巷,走到村南河沿上,这里有一个挺大的场院。场院周边有几个麦草垛,中间偌大的一块地方,不知被谁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场院中间,用三根打场杆子支起一个架子,架子上挂着一盏保险灯,周围坐着男男女女好多人。女人们手里大都掐着草编,男人们手里都摇着蒲扇。那保险灯的一旁,摆着一桌一凳,桌子上有一把茶壶,一个茶斗子。此刻有个身穿白衫的青年人站在桌前,他一手持扇,一手比划着,他正在说书。说书人虽然用的是方言,但是那声音洪亮,吐字清晰,抑扬顿挫,声情并茂。仔细一听,明白人便知道他说的是《七侠五义》。听书的人们鸦雀无声,不眨眼地瞅着说书人,脸上那表情时而紧张,时而放松,时而忍俊不禁,时而哈哈大笑。当一回书说完,人们便大声喝彩:“说得好!赶快喝点水,润润嗓子,接着说下去!”这时便有人走到说书人面前,给他往茶斗子里添水。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在离场院不远处,有一大片雪白的沙滩,那沙子如同被清水淘洗过一般,沙粒都很圆润,如同白芝麻似的。宽大的沙滩上横七竖八地铺放着麦草帘子或蒲帘子,帘子上躺着清一色的男人和孩子们。这大都是些不喜欢听书和不爱凑热闹的人。他们或侧卧或仰躺着,手里悠闲地摇着蒲扇。河风有一阵没一阵地轻轻吹过来,虽然略有凉意,但人们却感觉能以透过气来。他们劳作了一天,却不觉着怎么疲乏,没有一点睡意。他们有的在侧耳细听,场院那边不时地传来时断时续的说书声和喝彩声;他们有的在仰望着东北天空,黑蓝的天空中,星星密密麻麻的,像波光粼粼的大河床一样美。他们用眼睛搜寻到了,天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。于是一边指点着让孩子们看,一边拉着长腔给孩子讲牛郎织女的故事;有点气象经验的老者,他们关心的是阴晴风雨。于是他们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北斗星,偶尔可见那里隐隐约约地打闪,便抓住时机向孩子们传授看天气的经验,说北斗星下面打闪,不过三日就会有雨。他们忽而又会指着正南天空,说看那里有一大一小两颗星,说那是大瓶儿和小瓶儿。要是大瓶高于小瓶,天就有雨了。这时候,东南天空中不知不觉升起了大半个月亮,而且还有月晕。老农们便把月晕叫做“月亮烤火”。他们指着朦胧的月亮让孩子看,很自信地说:“看看吧,月亮烤火,下一小钵儿。”意思是说有了月晕,明后天就要下雨了……这也属于看天象识天气呢!老者们的这些说法,十有八九是准确的。因为这都是一辈又一辈人详细观察气象而积累的经验。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盛夏之夜,天气炎热,人们大都睡觉晚。大约过了十点多钟,便有父母呼唤自家的孩子回家睡觉。可孩子们大都不愿意回家去睡。他们大都躺在帘子上不肯起来。于是有父母便大声呵斥:“起来起来!回家去睡!”可孩子们还是赖着不肯动。有父亲一边呵斥,一边轻轻地朝孩子的屁股上拍几巴掌:“快起来,回家去睡!”孩子们为啥不肯回家去睡?因为大多数人家都没有蚊帐,也没有驱蚊蝇的药物,更没有风扇和空调。家家户户需要点上用艾蒿之类的植物拧成的“艾绳”,使其冒烟来驱赶蚊蝇。家家屋里都是一天三顿在大锅里烧火做饭,烧的又是柴草,那烟火直通到炕洞里,因此那炕就像烙铁一样热。再加上蚊子、臭虫、跳蚤叮咬,怎能睡得着觉呢?
可是,孩子们在大人的再三催促下,他们极不情愿地从帘子上爬起来,身子软软的,一手抹着眼睛,磕磕绊绊地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父母回家转。
刚一走进屋里,马上就感觉如同下了蒸锅一般,汗水便立刻冒出来。然而,他们不得不忍受着那呛人的艾蒿的浓烟,极不情愿地躺到那热呼呼的土炕上去,像烙小鱼一样地翻来覆去。孩子们毕竟是乏了,不一会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大约十一点过后,大街上,场院里,河滩上,乘凉的人们便陆续散去。盛夏之夜的老村庄,便渐渐归于了宁静。这时候大街小巷里,便弥散着艾蒿那特有的淡淡的清香。
 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图源:《莱韵风华网》
——《莱韵风华网•文心雅韵•散文随笔》栏目组编辑
文章点评